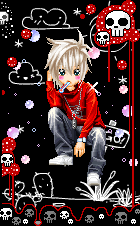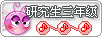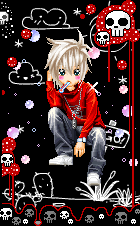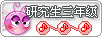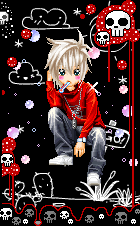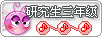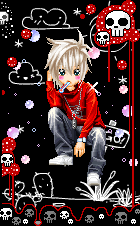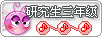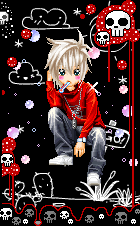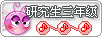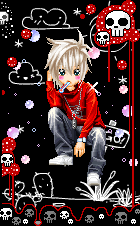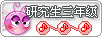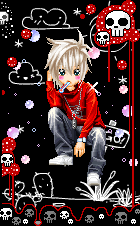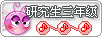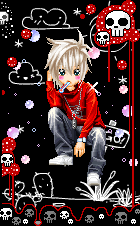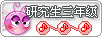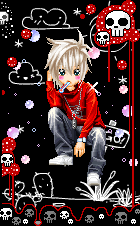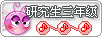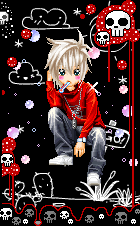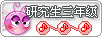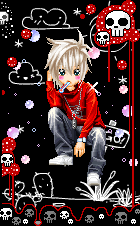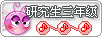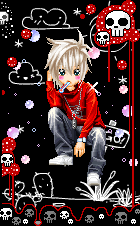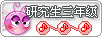血流出来后,就变成了水。她执着而迷茫。天很灰暗。她等他。但是她知道他不会来。他留下了房门的钥匙。暴风骤雨般的争吵骤然平息。她的肌肤很疼痛。所有的记忆的碎片不再闪光。她的心很累。眼睛干涸。在争吵中他qb她。他拼力撕扯着她的衣服,他以为那样就能抚平她心上的伤痛。做爱早已成为了形式。维持着两个无望的肉体。一切依然如旧往。他紧紧地抱着她。然后他走。义无返顾仿佛古罗马的勇士。他周身铠甲。手里是一块残破的盾牌。她想哭但没有眼泪。分手很艰难,但他们最终还是做出了选择。六年里他们曾一千次说起过分手的事,但却一千次没有行动。但是这一次不同了。她守着电话但知道他再也不会把电话打来。这一次他们已经彻底分割,衣物,连同身体。
从此他们只属于自己。
从此她不知他的音讯。
她化妆。因为她必须要出席一个专为她举行的招待会。她不知自己至今仍参加这样的所谓活动是不是很无聊。镜中的她苍黄丑陋。细碎的皱纹密布着。为此她本不该与他为敌,但是她做不到。她无数次大声宣布有人会爱她。他便用一只手掐着她的脖子说,那你就爱去。她的确收到过情书,那些痴迷的小白脸们。她没有骗他,那是因为他们喜欢她写的书。但是她把那些情书全都撕碎后扔进了抽水马桶。她认为那些纸片比起他的爱来微不足道。她为此而觉得对那些写情书的人们很不公平。她满怀着歉疚。就为了忠诚。而忠诚是为了爱,但她已无法证实他们之间是否还有爱。他们已身心疲惫。他们不爱但却要无奈的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她曾经以为那就是爱,为他们的每一次做爱激动良久。
如今他走了。在房间里留下了一个男人的气息。她说不清自己是不是想念他。她只要求着自己应坚持他们之间的这可怕的距离。她再没有去找过他也没有打过电话。她只是细心地化妆。她化妆时总是很投入。她热衷于在清晨或是在午后改变一种形象。她这样终日里浓妆艳抹是因为她确乎知道自己已经老了。她穿领口很低的黑丝绒长裙。这是她一贯的风格而他作为一个男人似乎从未干涉过她。她认为她的肩和背都很美很性感,所以她总是在温度允许的情况下尽全力裸露那些美丽性感的部分。其实这样做她并不是为了别人而只是为自己。当然如果一定要为了什么人的话,那么她想她六年来可能一直是在为他。但是他却似乎从未对她裸露的那些部分动过心。他看她时竟从未用过性的感觉和目光。他们彼此太熟悉了。他熟悉她身体上的每一寸肌肤。她觉得他对待她就像是一个外科医生,这是她时常感到遗憾的。但她还是坚持着裸露,坚持着那种裸露之后的自我感觉。
镜中的她慢慢变得靓丽。无疑是化妆品帮助了她,所以她常能听到有人恭维地对她说,你真是越来越漂亮。她问,是吗?然后她紧接着又说,不,我老了。但尽管她说她老了,她还是一直相信她自己是很漂亮的,至少是很有味道。
然后她去了那个大酒店的招待会。她被人簇拥着走进酒店大门的时候,突然有了种茫然若失的感觉。她停住脚步。她马上意识到那肯定是因为他。他从此不会伴她左右了,她要独自一人面对世界。她因此而感到有些恐惧。她的出版商女老板慌乱地跑出来。那个有点三教九流味道的女大款一把抓住了想逃跑的她。然后她被亲切而虚伪地拥抱着。女老板对她投以无限同情爱怜的目光,并轻轻拍着她裸露的后背说,总会过去的,你不要紧张。
她挣脱了女老板散发着金钱味道的怀抱。她说,对不起,她不能哭,因为她精心地涂刷了睫毛膏,尽管这睫毛膏是防水的,但是她还是不哭为好。然后女老板为她介绍各类新闻记者。在锦簇花团之中,她觉得自己立刻进入了状态,且如鱼得水。她忘记了他。尽管偶尔想起也是怀着一种报复般的快意。她想,生活中其实不见得非要有男人。在晃来晃去的人们的目光中,她还是感到了自己是怎样的光彩照人。她的削瘦的脸颊和猩红的嘴唇。她觉得“性感”和“迷人”是对女人最好的赞美,而她此刻正体验着这两个词汇的意味。她寒暄着。她很会这一套。手里端着那琥珀色浆液的透明高脚杯,她觉得这是一种很令她迷醉的境界。
她的成功表现在主席台前摆放的那一本本用红丝带捆扎起来的她的那本新书。新书是写给女人们的,书的名字叫《不可摧毁》,可连她也不知道这世间是不是还有什么是不可摧毁的。但是当记者问她是不是有成就感的时候,她马上说她没有。她真的没有。她说当她第一次见到这本印好的新书时,她真想把这书撕成碎片。她说“女权”是一个很混蛋的定义,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而这本新书就是“女权”的牺牲品,她告诉记者,这一点只有她自己清楚。
简短而又辉煌的仪式开始了。要她站起来说几句的时候,她想这是她表演的时候了。于是她装作很有风度的样子站起来,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功成名就的亥作家,并且用纯粹作家的腔调发出虚伪空洞又哗众取宠的呐喊。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什么为女人写书呀,什么蒙读者厚爱呀,什么感谢出版者呀。于是有记者问,你用这本书究竟换了多少钱?多少钱?她一时语塞,但马上又想起一个作家所应当拥有的机智。但是她没有机智。她根本就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于是她照实公布了那数字,她说是的,有很多钱,足以支撑我奢侈而无聊的生活了。但是今天这钱对我已毫无意义。他已经走了,他……
全场哗然。
她不管别人怎样看她怎样议论她。她认为自己早已经超越了被风言风语所控制所左右的年龄。
她站在那里继续说,我卸过妆之后就是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我讨厌在这里表演。也懒得看你们这些人表演。表演很累。装腔作势很无聊。你们何不在家里在床上做点有意思的事。你们以为人生是一场什么?是一场戏吗?是妓院或是战场?《不可摧毁》什么也不是。真的,那书里全都是谎言。
女老板很紧张地请录音师放响了音乐。她希望那些或激烈或舒缓的音乐能压灭与会者对她的愤怒。她也很愤怒。她扭身离开了那个嘈杂的会场。没有人理睬她。她知道这意味了什么。她讲了真话。她随便叫了一辆出租车。就在她扭转头的时候,她看见了A。
A?
简直是奇迹!
A已失踪多年,所有认识A的人都相信A已经死了。
真的是A吗?A有点面目可憎地站在街边。她疑惑自己是幻觉或者是撞见了鬼。但是她确曾崇拜过A。那时候她还很年轻。A是她唯一爱过的也是唯一没有睡过觉的男人。后来他们彼此仇恨,再后来A就销声匿迹了。
她叫住了出租车司机,叫他把车停在街边。她走向A。在暗夜中。她看见A胸前抱着一把陈旧的吉他。她用手去摸那吉他上已经生锈的银饰。她再度感受到A仇恨的目光。她问A,你愿意陪我回家吗?她说她现在已孤身一人,在她与A之间已没有障碍。她从自己的声音中听出了孤立无援和厚颜无耻。她猜A也一定听出了这些。但就因为这些她就要放弃A吗?不,她好不容易才找到A是很多年才如流星般在她眼前闪过的。而且会一闪即逝,落在不知多么遥远的深谷中。她继续说A,跟我走吧,我请你喝一杯咖啡。
A在她的请求中背着他的吉他扬长而去。A一贯喜欢在女人的请求中自高自大,以满足他无聊的虚荣心。她被孤零零留在街边的冷风中。她低头看见了A遗落在那里的一个装着硬币的纸盒。A以歌为主。A的生涯使她心里顿生柔情。
出租车司机在奋力按着喇叭。
她捡起A的那纸盒。一路上,仿佛总能听到A的歌。
A的歌声是在半夜响起在走廊的。
一开始,她以为是在做梦。她在梦中惊醒。她想A是个疯子。她为了不影响邻居立刻打开了门。但是邻居们已经都披着睡衣走出门来观赏A了。
A你要做什么?
她想不到A就坐在她的对面,就像很多年前那样。他离去后,A便出现,她想这简直是天意。她穿着真丝的拖地的睡裙。那睡裙是淡粉色的。背后是几组交错的细丝带,很性感地将她的肩背和腰部暴露在温暖的灯光下,她告诉A,这睡裙是她为自己买的。
她拉起A的手来触摸她的睡裙。她说尽管我们已经有整整十年没有联系了,但我们并不陌生。她说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死了。后来我有了另外的男人。他一直障碍着我想念你。但我是想念你的,或者白天或者黑夜。我不知你是属于白天还是黑夜。总之际是唯一的没有给我身体的男人。在那一刻,你逃走了。你把爱留在了精神的崩溃中。所以才永恒。所以我才一直把你悬在那个我无限珍爱的半空中。我一直想,倘若有一天你突然出现,我是不是会离开他跑去和你生活。我时常地这样想。即或是在他的怀中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就不再想了。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以为我们很相爱。但是我们并没有结婚。就这样我们拖延着直到分手。
A偶尔拨响他的一根弦。那弦发出很空洞忧伤的回响。
她把他的照片拿给A看。她问A照片中的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帅。
她给A讲他们的爱情。她说是很惊心动魄的那一种,包括他们之间的争吵。她说每一次他们之间的战争到来的时候,他都恨不能杀了她。
然后A突然站了起来。他猛扑过来紧抱住她的身体并拚力撕咬着她。就像是一头凶猛的鬣豹在撕扯吞食着一只羚羊。她的淡粉色的真丝睡裙被A扯得七零八落。她挣扎着。A是一个在残食着同类的野兽。很慢的但却很有力量的像电影中的那些慢镜头。A和她搅在一起最后将她折磨得遍体鳞伤。她独自哭泣。就像从前那样。那一次是在一条闪亮的河边。A无情地煽动起她的欲望,A在做着那一切的时候却满嘴的马丁·路德·金满嘴的理想宗教和崇高。她很疼,但是她竟以为那伤痛能证明她和A的爱。像杂草一样的灵魂越漂越远。唯有她是罪恶的。那一刻她被陷在罪恶的欲望中,她觉得其实她很想要A。河水中的光斑闪在了蔚蓝色的天空中。她记起了,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季。那蓝的天很清澈很高很旷远。
而就在此刻,A又旧戏重演。
她终于推开了A,她一步步地向后退着,她碰倒了A靠在墙边的那把吉他,那声响将所有的旋律在瞬间奏响。她很怕。她继续退着。好歹拽着那淡粉色的碎片遮掩着她遍布着伤痕的身体。
A睁大着眼睛。A一步步地逼近她,她看见了A眼睛中的那一道道血丝,那血丝组成的网。她说不,不要,她说A其实这正是她旷日已久盼望的。她足足等了A十年,但她此刻还是请A先离开。
A问为什么?
女人说,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这房中还有着他的气息。她说,A,那样对你不公平,我的心还没有属于你。
她找到了他前妻的那封来信。那信她过去已读过很多遍。那是一封充满了缠绵忧伤但又很超然很达观的信。那信中说,他们曾相爱,爱了很多年。没有比他们的分手更令她苦痛的了。但是她尊重他的选择,并希望他未来能幸福。这信来自异国他乡。密密麻麻地正反两张外国纸。那信曾经很刺伤她。在那个晚上,她与他做爱时她问他,你是不是依然很爱你妻子?
他说她已经不是我妻子了。我们离婚了,这你知道。
但是她说她爱你。
是的,是爱过,那时我还没有遇到你。
但是你们爱过。
那已经是历史了。历史怎么会改变呢?
她说,我知道。历史当然不能改变。
她挣脱了他的怀抱,她拒绝了他。她觉得她简直无法承受她正爱的这个男人过去却被别人爱着的那历史。她很痛苦。在暗夜想象着他们过去做爱时的情景,想象着他是怎样紧搂着另一个女人怎样地把最终的快乐给予她。进而她猜测他一定还爱着他前妻,他是不得已才告别以往的,所以他怀念以往。这念头使她无法忍受,她为此而拒绝他,拒绝他的臂膀他的嘴唇他的身体和他的热望。最后他被推到了床下。他拉开灯,他说你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就为了那封信吗?事实是她已经宽容大度地和我离了婚,你还要怎样呢?他说你这个女人最可恶的地方就是臆造苦痛折磨自己和别人。
然后他愤然搬到另一个房间,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了大床上。她醒着。她想她还要什么呢?他已经为她和远在国外的妻子离了婚,他已经从那舒适的生活中返回,已经完全彻底从形式到本质都属于她了,可她还要什么呢?几年来她一步一步地要他、逼迫他。她要他的爱,他的身体,他的痛苦的离异,可这一切她全都得到了呀。然后再要他什么?他思维中的每一个瞬间。她要他今后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只想念她一个人,但是他能做到吗?
因为做不到,他们才争吵。
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自私的残酷的女人。她也从不想从此就扼住他的脖颈。她不懂他为什么总是抱怨喘不过气来。后来他们才发现是因为爱太残酷,让人在身心疲惫中变得自私。然后是厌倦。厌倦很可怕,是厌倦使他在日渐麻木的生活中怀念以往。她坚信这绝不是她臆造出来的。她已经在他的眼睛中看到了那丝丝缕缕的牵念……
她终于不能独自醒在凄冷的黑暗中。她从床上爬起来扭亮了房间里所有的灯。她在灯火通明中赤身裸体闯进他睡觉的那个房间。她猛然间掀掉他身上的被子。男人被惊醒。她大声喊叫着,不——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战争开始。女人的武器是说出各种刻毒的诅咒的语言。男人无以抵挡便把那个毫无掩掩的女人的身体撕扯得鲜血淋漓……
当他们终于搂抱在一起躺在床上时,天空已开始明亮。
男人很伤感。他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夜晚?
女人哭着,她说,我只要你的心。
她没有朋友。但是S来了。S说,只有女人最能理解体贴关心和爱护女人。我早就说过,女人应当和女人生活在一起。你指望他什么呢?他想的和你永远不一样。他考虑的是尘世中的所有事物,但绝不是你的这颗心。
她听S讲话总是感到很茫然。
那晚S住在了她家里。S充当着牧师的角色,而她那时太需要有人能给予她安慰。S是心理医生。她披着心理医生的道德外衣,内心却充满了对男人的仇恨。S很可怜。她的男人在某一个早晨彻底抛弃了她。那晚S出差。她清晨用钥匙打开门锁的时候,正看见她丈夫同另一个女人在她的床上。这一幕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很可怕的。S愤怒以极。尽管她那时早就和她的丈夫分床了。使S愤怒的是他们竟然不在她丈夫的床上而是在她的床上做爱。S嫉恶如仇。但是她想不到当她去找那个与她丈夫做爱的女人理论时,她们竟成了朋友。是女人的不幸联结了她们。后来那女人告诉S,他们之所以在S的床上是因为他丈夫认为那样更刺激。他说他在S的气息中同另一个女人做爱就更加讽刺了他与S的同床异梦。这讽刺使他兴奋。他为能背叛S而性欲旺盛。S认为她丈夫肯定是在心理上有问题。于是在离婚后便挂牌做起了私人诊所的心理医生。她医治的所有病人都是女人,她接手的所有病例也全都是男女之间的爱情纠纷。S英勇无畏地为所有的女人伸张正义,向男人讨伐。S从不同性相斥,相反她越来越和她的女病人们亲密无间。她爱她们。经S医治的女人全都变得坚强和独立自主了起来,而原有的情感最终均告破裂,因为这些女人再也不需要依赖男人。而本质是,S在她的每一个女病人身上都实现了一次对男人的报复。
她了解这一切,但她还是去找了S。S是她的大学同窗,她们一直共同住在一个女生宿舍里,但她从未发现过S有如此气魄。S后来简直成为了她的女病人们心目中的神。她去找S是为了她的那部关于女人的小说《不可摧毁》。S确实给了她很大的帮助。“不可摧毁”这个很女权味道的书名就是在S的鼓舞下想出来的。
S说她是在报纸上看到她的感情悲剧和她的混乱状态后才来看她的。整整一个晚上,她向S诉说他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情感。苦难与变迁。她一直在哭。S说,她很值得同情,因为她并不是一个自立的女人。她的苦难是她自己造成的,因为她主动去做了男人的精神的囚徒。然后夜深人静。她去洗澡。她洗了头。坐在床边。这时候S推门进来。
S走到离她很近的位置上。S顺手关上了房间的大灯,扭亮了床边的小灯。S走近她并抬起手臂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S说,别折磨自己了,你看你的头发已变得枯干稀少。她又哭了。很辛酸。她想起他每年秋天都会为她头发的脱落而扼腕叹息。那一根根柔软而长的黑色发丝同秋的叶一道飘零……她真的很辛酸。她靠在了S温暖而丰满的胸怀中。她说,再没有人心疼我。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不可摧毁》。他也永远不想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S,我……
S搂抱着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背,摇着。她在那一刻骤然有了种儿时被母亲抚爱的感觉。为此她感谢S。她甚至相信那么温暖的毫无邪念的爱抚一定能平复她心中的苦痛。她被S轻轻地摇着,她听到S用最温柔的声音对她说,你是我们的姐妹。到我们的生活中来吧……紧接着,S把她抱得更紧,S的手臂也变换了位置。她很惊惧。她骤然挣脱了S,从床上跳下来。她睁大紧张恐惧的眼睛看着S说,S,我还是到另一个房间去睡吧。我们离开有半年了,我已经不习惯和人同睡一张床……
她不想伤害S。但是她不懂为什么,似乎所有的温暖都一定要伴随着要求和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