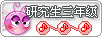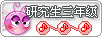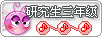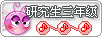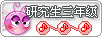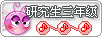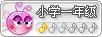学历和封面
首先得说明的是,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并且也不觉得成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本身就是愚蠢的表现。不过,由于我读过的多所中美学校,它们的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倒不完全是外行。
对于有些学校或有些人,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方面实质上和其他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的名誉过日子,和书有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大(教学深广度有较大差别的除外)。
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19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以后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却去的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经常验证这样的常识:每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人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内地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一般的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有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究生后,不久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研究生,博士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是出于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和他在中国大学的训练没有关系。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
我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他近年来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觉得他的专业成就是由他自己的能力决定的。
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在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方面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到了作用。
二十多年前,北大生物系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就很少(在中国生命科学里研究杰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科院),也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给予特殊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可以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母校时,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地不同于中国其他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时间有关系。对于有些专业的学生,有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不过就我所知道的生命科学领域,这样的情况即便不是没有,恐怕也很少。
就是在美国,哈佛也不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的来自多个学校的学生中,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是我在哈佛见到的学生。当然我直接接触的学生人数有限,不具有统计规律。
在中国和华裔社会里,常常有人很关心某人毕业的学校,甚至因为学校而影响到人的关系。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术精英群体里,对个人在专长上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就读过的学校的关注。美国特别好的学校,对中国各个学校的了解,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旁边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听说了,也难有感性认识。这就好比中国学校不知道印度学校好坏一样,没有印度人解释,中国人自己不会有强烈印象。
在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录取委员会上,大家都重视学生的具体表现。我们录取的美国学生,有名牌大学的,也有名字都难以记清楚的学校。几年前,我们曾拒绝过一位中国名牌大学的申请者,虽然她所有的分数都很高,却说不出为什么对研究感兴趣。在美国和加拿大学生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当然反过来,美、加学生中也有人在我们学校录取后,却拒绝我们而去名气差很多的学校。但是他是奔某个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领域而去的,我们也觉得这样的学生作出了合理的决定。
有些华裔家长拼命要求子女进某些特定大学,以便其后能进好的医学院或研究生院,在我看来也是过度操心。这些医学院和研究生院并不是按照一般华裔家长的标准来招生的。华裔家长压学生上某个或某种大学的做法,实际上既不利于学生的自然成长,也不一定有利于达到家长以为的好的目标。我在哈佛碰到过华裔大学生,有些对家长怨声载道,上大学以后有逆反行为,家长自以为是的好心反而成为他们发展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