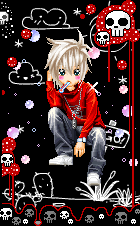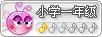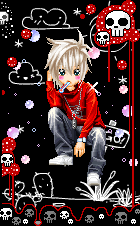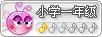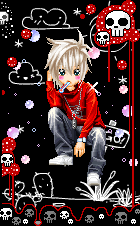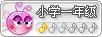综合厂弹花车间有一位弹花工叫王康,曾参加过大方川剧团唱过戏,曾义请教他学琴的事,他嬉笑嬉笑的对曾义说::“你看你自己那一双手,像玩乐器的?!手指头像红萝卜,比琴的品位还宽,拳头像弹花的手槌,你只是弹棉花的料了。不要糟蹋音乐喽。”
“品位是哪样?”
“这都不懂?出音高低的格格!”
“你不相信我学得会乐器?”
|
“不相信。你呀,肚皮大脖子粗,学吹撒呐还要得。”
“吹撒呐?我又不去做下祭的事,土里土气的。你不要奚落我。”
“哎?土?你就去学洋的,去学吹洋号!大定城还没有哪个吹过洋号呢!你吹好喽,全县出名。娘娘们听到后,赶倒你的屁股追!”
“没有老师教。”曾义还当真了。
“有一个,以前和我在一个戏团中打钵的,现在食品公司上班,姓徐,徐麻子,当过兵,在部队是号兵,它可以教你。”
过了几月,曾义还真托人买了一把旧小号,去拜徐麻子为师了。徐麻子对曾义学吹号,定了三条规矩:早上6点起床,不准屙尿;每天早上喝一个生鸡蛋;一天吹一个长音,一直要把尿吹散。曾义照做了,夹尿夹在裤裆里的时候都有,自己也不敢声张。练了三月长音,的确有进步,嘴皮吹硬了,加上自己中气又足。吹起来,还很拉山的。
曾义要请徐麻子教他吹歌曲了。
徐麻子是吹军号的,不会识谱,再说军号没有米米按,一根管子通号口,只能吹出音乐中的索多米索多,吹不出来发拉稀。既然是老师,也不掉架,徐麻子要求先学不按米米的吹法,第一首曲子就是国民党军队的起床号:米索—米多—索米米多米—米多索索。
徐麻子学号时,也不是用谱唱,而是部队司号教练教的先用嘴练词:死猪—起床—猪死在床上—起来冲锋。。。。。。这一教,曾义还真有点兴趣,每天早上练号,就吹起床号。
曾义会吹歌了,会吹起床号。
接着学会的第二首,就是冲锋号。
学了一年,徐麻子没有教曾义吹歌曲,曾义心冷了,学号的事也搁下来了。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手工业联合社成立了造反派组织“红色工人造反团”,在其他人的鼓动下,曾义去领了红袖章带上,成了造反派。造反团几乎天天都有会开。要么誓师大会,要么批斗会,很热闹,又风光。曾义有点“乐不归弹”了。
69年,大方两派开始武斗了。红色工人造反团一伙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工人赤卫队敢死队的主力军。弹花匠王康当上了敢死队教练,是因为他演戏时学了几招花拳绣腿。这时,为了鼓舞斗志,王康把曾义派上了用场。敢死队统一食宿,曾义当上了号手,恰巧自己学的起床号、冲锋号刚好够用。
但是,王康不满意曾义的现有水平,勒令他半月之内会吹几首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王康还说,不会吹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这是革命立场问题。曾义还有点怕“革命立场”这顶帽子,到处打访,终于在毕节找到一位会按小号米米的老师,教会了他找音阶。经过半月的苦练,终于会吹一首毛主席语录歌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首歌简单,只有两遍重复,最后一遍还是用念。
六龙武斗,工人赤卫队被打死三名队员。工人赤卫队把三具尸体抬在县城大十字百货大楼门口,在搭建的辩论台上搭起了灵堂。封资修、迷信的事不能做。这回工人赤卫队只有唱革命歌曲来守灵。这时的曾义的确在山城火了一把。队员们唱累了,就该他吹语录歌:“下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