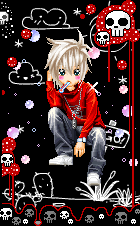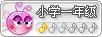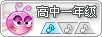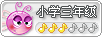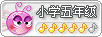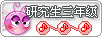谁是那个神秘的杀手?
――读《山花》2007年第5期肖铁小说《受伤现场》
肖铁的写作看起来是很传统的,然而他想表达的东西并不传统。《受伤现场》的深度远离了文本的话话系统。记得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那么肖铁可以说已经做了蕴藉,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很多年轻的写作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笨掘。肖铁观察生活的细致可以从另一个作家范小青的写作中感受到。
《受伤现场》写的一是次平常的同学聚会,是一种被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然而,肖铁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之中,用他那十分容易“受伤”的神经,触摸到了现实的荒谬性存在:人类力图恢复记忆的努力不过是徒劳的,存在的本质永远无法接近,越是靠近它其实我们离它可能越远。
一次同学聚会,共同的记忆自然是必有话题,这也是团聚的理由。然而,那些过去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是不一样的,同学间的近距离亲密接触,却不过是再次确认其实他们的心里的距离其实有多远。比如,“我”和同学“扁皮”按约去参加这次同学聚会,却发现记忆中根本没有这个叫栾新的同学任何印象,“我”和扁皮的对学生时代的一次恶作剧的记忆,与柳梅对同一件事情的记忆根本没办法重合。我对宣传委员“大豆眼”的印象,被她完全否认。这些前来参加聚会的同学如此陌生,已经面目全非,如同一面打碎的镜子,一场同学聚会本来是为了接近彼此的距离,却让大家发现其实大家是如此陌生,如此疏远,在心里感觉到:一切,早就已经过去了,虽然构柳梅小腿上那个浅浅的疤痕还在。
所以,必须要有一些方式,一些活动来调集大家参与,衬托这次聚会的表面的热闹。参加这次聚会的个人玩起了“杀人游戏”。在这次聚会中,有个叫严兵的当警察的人虽然没有来,但却让人觉得他无所不在。在这次无聊的游戏中,大家假装调动起激情,然而,事实却让是,根本不是同学的柳梅的丈夫老赵居然成为“我”觉得最有亲切感觉的人:“在这么一位肯定是从未谋面的老赵身上的这种熟悉感,不得不让我怀疑起这次同学聚会,及及自己参与的意义。”想想,一场本注应该热闹非凡的同学聚会,却被沉默、僵局、陌生的气氛包围,要不是一种娱乐性的游戏。大家无共同话题可说,而“我”想接近距离的交流努力,却因为彼此记忆的差异而失去气力。聚会是为了找到过去的“共同存在”,然而“我”悲哀地发现,这种场原来不存在。“很遗憾啊,这么快就出局了。但这种意外性正是这种游戏的迷人之处啊,活着的可以继续体会,互相帮助体会。”往昔不可重复,正如游戏中第一个被杀掉的栾新说的这样,我们要“互相帮助”才能“体会”,才能把这次聚会勉强玩下去,真是可悲。
应该说,肖失很会讲故事。他十分熟谙于叙事技巧,能够在引起读者的阅读期待之后,在原地成功转身,看似顾左右而言它,却紧紧地抓住了展开故事绳子,把情节穿连得恰到好处。小说中的第一个“受伤”,是学生时代“我”和李便平企图捉弄同学严兵而挖了个坑,结果却让美丽的柳儿受伤,反而给严兵这个狗家伙以献殷勤的机会,柳儿的受伤只是在腿上,而“我”的伤却是在心里;接下来,我遭灾了严新在我到水龙头边喝水时,进行了报复,我的嘴出了血,这是第二闪;第三次,却是在这次聚会上,柳儿一直以为那个在她的课桌里放豆包的人的严兵而事实却是我,让我再次受伤。《受伤现场》就是这样把受伤的侧面一点点展开来的。
然而,肖铁的意味并不仅仅在这里,小说对“杀人游戏”的描写,才是真正的对“受伤现场”的展示。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不但引人思考,对人物的心理把握也十分到位,肖铁对这个“现场”的“特写”是成功的。小说中,那个让我的嘴受伤的当警察的同学严兵自始自终没有出现,然而却无时不在“我”的感觉之中。一场“杀人游戏”为主要剧目的同学聚会,“警察”缺席了,“法官”(老赵,柳梅的丈夫,算不上这场聚会的主角)却不过是个看客,吊诡的中,最后肖铁并没有告诉我们谁是真正的“杀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杀手应该是“时间”这个东西。记忆不过是对时间的再现,然而由于人个体的差异,时间给我们的是不同的记忆残片,而且似打碎的镜子一样难以收拢,是时间否认了我们的过去,现面,甚至未来,它让我们看到了心灵靠近的不可能性,他才是真正的凶手!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注定是孤独的,这就是我读这篇小说的得到的启示。
记得狄尔泰有一句话:“我们这一代,要比以往受到更大的推动去试着探索生活的神秘面孔,这面孔嘴角上堆满了笑容,便双眼却是忧伤的。”(《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出生于70年代末的肖铁的这篇小说具有忧伤的先锋气质,表现出了与80后作家不同的惊人的文学才华。肖铁另外的一个长篇小说《火车!火车!》最近引起了较大反响,得到很多正面的评价。正如徐坤博士所说,“也许若干年后,等到80后这一批新锐写手走过许多成长的歧途、终于回归传统文学写作路径时,才会有批评家讶异道:咄!何消等待这许久!那个名叫肖铁的年轻作家,早在这个世纪的第七个年头,就已经以《火车!火车!》这部小说宣判了新老艺术家的殊途同归,宣告了他们那一代人告别青春梦、步入沉重成人写作之途的开始”,从这篇短小的《受伤现场》中,似可见一斑。